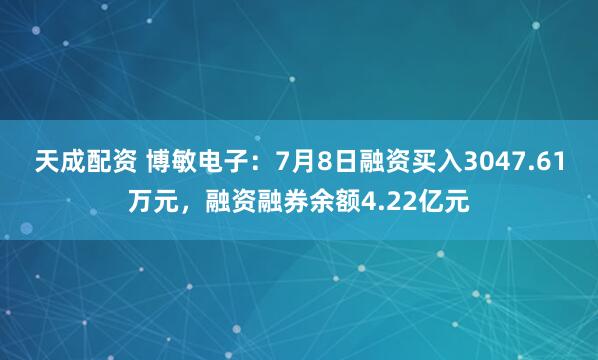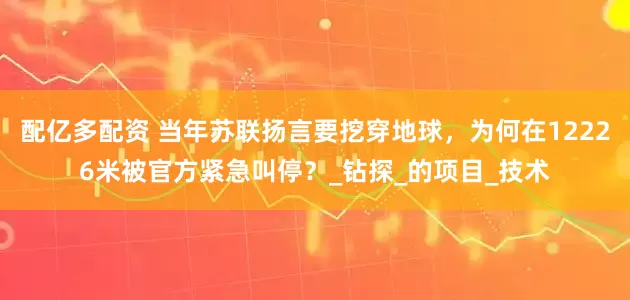天成配资 “散装”浙江话_方言_吴语_温州

昨天,我们探讨了,勾起不少读者对一口乡音、一片故土的深厚情感。今天,我们再将目光对准一个有趣的现象——“散装”浙江话。
浙江话到底是什么话?答案可谓五花八门——“石骨铁硬”如宁波话,坊间戏称“宁听苏州人吵架,不听宁波人说话”;温婉软糯如嘉兴话,即使红脸争吵也给人低吟浅唱的感觉……其实,按照地市划分已是比较粗略,作为全国“话最多”的省份之一,不说邻市之间仿若“鸡同鸭讲”,同村不同话也并不稀奇。
有诗人说,“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”。方言也是如此。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“散装”的浙江话和它背后的地理人文。
浙江湖州两位老人在聊天 图源:视觉中国
一
若是画一张浙江各地的方言地图,会发现,吴语在浙江省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有研究显示,浙江省内吴语的使用人口占比约98%,其余各地的方言则包括官话、畲话、闽语、客家话、赣语,等等。
展开剩余82%不过,网友也创造了一个新词“吴语渐无语”,意思是,就算大家都在一个语系也不一定能顺畅沟通。这是为何?
原来,吴语可以分为六大片区,太湖片、台州片、瓯江片、婺州片、处衢片、宣州片,每个片区都在浙江省内有所分布。其中,太湖片又可以细分为六个小片:毗陵、苏沪嘉、苕溪、杭州、临绍和甬江,比如“说起话来像吵架”的宁波话就属于甬江小片。
2015年,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时,浙江入围全国四个试点省市。起初,根据“一县一点”的原则,项目组只确定了77个方言点,之后经过实际调研,又增加了11个方言点。换句话说,浙江省现存88种方言。
浙江为何“话多”?究其原因,在于不同县乃至不同村的方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调调。比如,同样说“太阳”,宁波人说“日头”,金华人说“热头”,衢州人说“平日”,到了温州人这边,又变成了“太阳佛”“热头佛”。
再如,现代汉语普通话仅有4个声调,而浙江各地的方言往往不止4个声调。以苏沪嘉小片的嘉兴话为例,共有9个声调,声调不同,话语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。海盐籍语言学家胡明扬就把家乡的方言划分出8个声调,还总结出一系列的变调群。嘉兴话之所以婉转,兴许原因就是声调众多。
也难怪不少浙江人出了县就会发现,尽管或多或少能听懂隔壁县的方言,但真要说起别人的方言,总感觉少了一丝“灵韵”。
嘉兴南湖 图源:视觉中国
二
浙江人也常自豪于本地方言。温州人常以温州话能当密语为傲。相传温州话曾被当作密语传递情报,被称作谍报史上的奇迹。传说无从考证,但“难懂”已然成了不少浙江方言的典型标签。
那么,浙江的方言到底为何如此难懂?明明大家说的都是吴语,怎么我说的吴语跟你说的吴语不一样?不妨从几处有趣的细节中找寻答案。
首先就是方言的渗透力。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,方言已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,在百年以上的时间线上考量,这已成为“积重难改”的语言习惯。
举个例子,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,林黛玉的《葬花吟》中“尔今死去侬收葬,未卜侬身何日丧?侬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侬知是谁?”一连用了四个“侬”字,是地道的吴语。此外,《红楼梦》中还把喝茶说成“吃茶”,把夹菜说成“搛菜”,皆为吴语的经典说法,而且现在浙江人还在沿用,可见这语言习惯多么根深蒂固、深入人心。
论起古音,温州话可谓代表语言。在温州,脸盆叫做“面盂”,早晨叫做“天光”,看似拗口,实则暗含古汉语的深意。温州话也因此被称为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。
此外,浙江地域不大,却是移民大省,不少移民的到来也催生了一个个方言岛。比如金华婺城区塔石乡的珊瑚村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“方言岛”。相传,清朝康熙年间,一位名为廖文仕的福建人来到浙江西南地区,立志要闯出一番天地,最终在汤溪县扎下了根,成就了今日的客家话方言岛。
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的地理特点,又天然地成为滋养方言岛的最优环境。比如,台州和金华被大盘山隔开,台州与温州被括苍山隔开,地理的界线成为了方言的界线。
当我们在调侃浙江方言多么难懂的时候,不妨把浙江方言这个“洋葱”掰开来细细品一品,或许能感受到夹杂着浓厚历史气息和地域文化的“甜味”。
温州瓯江 图源:视觉中国
三
曾经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:语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。然而,目前不少方言逐渐失去原本的文化土壤,陷入濒危的境地。这在难懂的浙江方言尤其是吴语上,表现得比较显著。甚至有专家学者论断,吴语很可能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。
幸而,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,关于浙江方言的调查研究持续进行,呈现出规模越来越大、调查越来越深入的态势。
1927年,“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”赵元任先生扛起了吴语调查的旗帜,在浙江设立14个调查点,开启了浙江方言调查研究的先河。新中国成立后,傅国通、郑张尚芳等多位语言学家先后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浙江方言调查,形成了《浙江方音集》《浙江方言的分区》等著作。
当然,二十世纪以来的大规模方言保护调查项目,莫过于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。在这之前,浙江省档案馆还开展了“方言语音建档”项目。
但这还不够。这仅仅是“治标”的方子,而非“治本”的良药。
有观点认为,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这种方言“没用”了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,这话不无道理。毕竟,方言只有运用在人与人交流的真实情境当中时,才算是发挥了它的实际效用,才算得上是“活着”的语言。否则,只会落得个“有些方言活着,它已经死了”的结局。
但从感情上讲,我们应该任由方言在现代化的列车上掉队吗?“周瑜陆逊久寂寞,千年北客嘲吴语”,有网友说得好,倘若连这咿呀古韵都消散而去,又该拿什么去讲述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故事?
方言是了解一方土地的人文密码。早在千年前,贺知章就写下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也许,这就是浙江话“散装”却依旧动人的原因所在——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,“乡音永远指引着我们找到回家的路”。
本文播音:王维琳
声明:稿件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。
发布于:北京市科元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